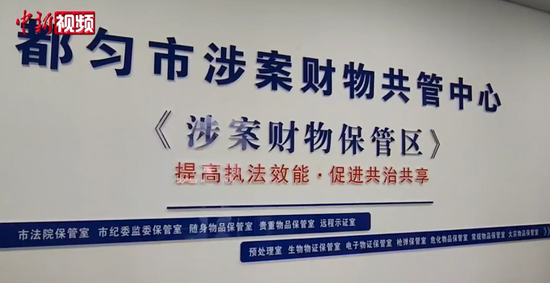贵州肖像·历史人物:南明弘光王朝内阁首辅马士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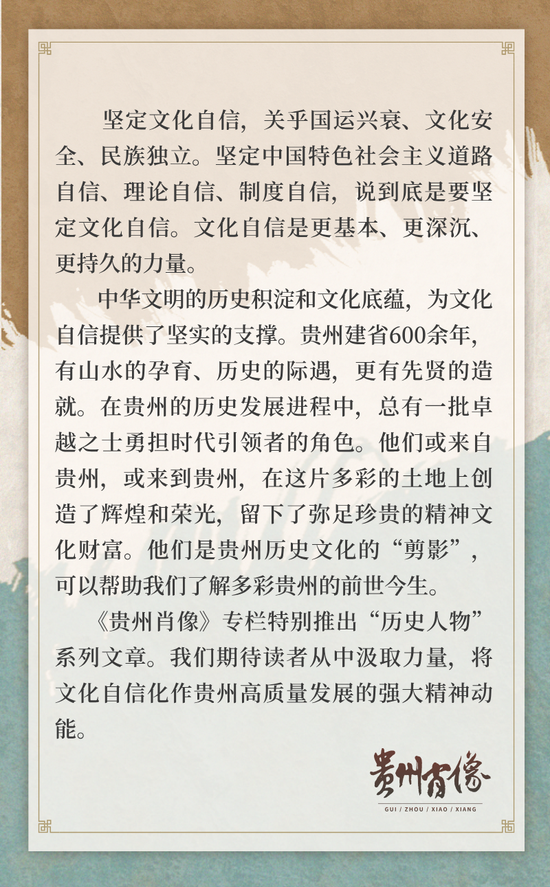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南明弘光王朝内阁首辅马士英
马士英,南明弘光王朝内阁首辅、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书画家。 字瑶草(一说字冲然,瑶草为别号)。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贵州(今贵阳市)人,祖籍淮南仪真(一说广西梧州)。入黔始祖马成,明初随军队至贵州,以军功官至指挥使世袭,遂为贵州人。马士英祖父马云龙,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字翔高,号腾海。父马明卿,曾任华阴县知县。马士英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
天启中,迁郎中,历任严州(旧名桐庐)、河南(旧名洛州)、大同知府。崇祯三年(1630年)至五年(1632年),先后任山西酉阳和道副使、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河北宣化)。到官才一月,因以公款数千金结交朝廷权贵而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坐遣戍”。不久,流寓南京,与阮大钺相遇。时阮大铖因“名挂逆案(魏忠贤案),失职久废”及慑于李自成大顺军逼近安徽而避居金陵,“颇以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由于两人曾是同科贡士,加上仕途失意,情趣相投,于是“相结甚欢”。
崇祯十五年(1642年),凤阳总督高斗光因失五城被捕论罪。礼部侍郎王锡衮力荐马士英“才堪大用”,于是朝廷复其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职,总督庐、凤等处军务。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兵败身亡,皇上命马士英进讨。马士英驱兵围城,刘超连连受挫,后活捉刘超,解往北京正法。十七年(1644年)3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5月,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李自成败走西安。是月,马士英与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炙手可热的朝廷重臣。
南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春,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马士英携太后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坚持抗击清军。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抗清失败后于太湖被清军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曾入四明山削发为僧,后被清军活捉,“剥其皮,实之以草,死极壮烈”,终不降清),享年55岁。
马士英于政务外,诗文俱佳,其诗比较清新活泼,杂着尽现其政治家的本色。其受到竟陵派影响,诗文创作提倡“静”“才”“真”“情”, 主张用我手去写我心,融入真情实感,不做无病呻吟。其文极少留存,仅有《永城纪略》《永牍》两篇传世,记征讨刘超事。但其工书法,长于行、草书;绘画以山水画为主,山水画师法董源,别有情趣,为明末著名画家。《画征录》有“画法倪(瓒)、黄(黄公望),颇足与思翁(董其 昌)、龙友(杨文骢)肩随”之语。时至今日,马士英作品已属罕见,其书画传世者见于《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的,有一幅现为青岛市博物馆所藏之《绢本山水》,另一幅为南京市博物馆所藏之《山水册页》,及南京市文物商店藏《赠杨龙友山水扇面》。另,安徽博物院藏有马士英《仿沈周山水图》,画置景远山近水,山下矶渚,坡壑横陈,呈现江天辽阔、水榭散落江渚之间,风情别具。而马士英对他的这幅画也很是欣赏,自题曰 “雨后临此”,形神俱似奇绝。时人评论此画构图采用一河两岸式的章法,近景洲矶空寂,杂树疏朗,孤亭兀立,中景秋水浩淼,江天辽阔,远景山岩层叠,峰峦如黛,全画笔墨松秀,意境萧索,风物冷然,在艺术上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末清初屈指可数的大画家,“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把马士英与杨文骢同列为明末全国著名画家,并称赞道:“晚年酷嗜 两贵州,笔声墨态能歌舞”,对其推崇备至。
明末有东林党,时常评议朝政,标榜清流政治、反对宦党余孽。弘光朝时期,也与当政者如马士英等不和。马士英在当政之初,也极力维持与东林党的关系,以此维护弘光王朝及江南一带形式之稳定。他起用不少的东林系人士,又极力表白他与东林党首领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从未与东林党人交恶,或打击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顾诚对之评论:“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一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是较为负责的历史 唯物主义评价。但马士英任首辅后,对其权力的欲望愈加强烈,也愈加嫉贤妒能,故即产生了他与领兵大将史可法的矛盾。当得知史可法执掌军国大事时,“以可法七不可”疏奏福王,并“拥兵入觐,拜衣即行”,逼迫福王疏远史可法,以达其独揽朝纲目的。出于维护内部团结,史可法忍辱负重,疏请督师淮、扬,出走金陵。史可法坐镇扬州后,总督江北军事,统辖四镇总兵,志在挺进中原,恢复明室。四镇之中,总兵高杰实力最强,被史可法所倚重。高杰打算由河南开州、归德进军,然后夺取中原,然而没想到住守在睢州的总兵许定国早已同清军勾结。清顺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年)正月,许定国诱杀高杰降清,致使史可法的北进计划成为泡影。马士英闻变,毫不顾及军国大计,立即任命亲信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接管了高杰部属,致使史可法实力锐减。
先是,马士英位极人臣,志得意满,“所畏者仅宁南伯左良玉一人 而已”。自弘光建号以来,南明小朝廷君臣不理政事,沉溺歌舞,引起朝野强烈不满。左良玉拥有数十万大军,住守武昌,是弘光王朝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反感马士英擅权,左良玉拥兵自重,便以“清君侧”为名,于清顺治元年(弘光元年,1644年)三月,举兵讨伐马士英。马士英不敢等闲视之,一面急遣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赴上游防御左兵,一面撤江北刘良佐等守军调往西边增援。当有人劝其“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时,马士英则呵斥曰:“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人犯耶?犹可议款;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时清军已定河南,弘光王潮以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淮、扬防卫虚弱,导致了清军的南下,4月,左良玉攻占九江,不久因病呕血而死。左良率兵进逼南京,谓“清君侧”,“除马阮”,实则在大故当前做煮豆萁之事。而马士英也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弘光王朝内部不统一 ,直接导致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殉难, 随即南京失陷,福王逃往芜湖,马士英率领400黔籍士兵,拥着福王母、妃逃往浙江,经德州,走杭州,弘光王朝毁灭。马士英后来继续在浙江一带,多次参与吴日生部的反清战斗,兵败后被清军抓获,最终不屈而死。之后,清军大举进攻浙江、福建及长江以南各省,南明鲁王、唐王等政权相继灭亡,只剩桂王即永历皇帝偏安西南,坚持抵抗,至顺治十八年 (1661年)最终失败。
马士英其人其事,明末以后,首先是一部《桃花扇》毁之于前,再是一篇《明史奸臣传》贬之于后,故一直是以大奸大恶传之于世。但史实并不是这样的。马士英在南明弘光朝掌握大权,确实也毫无大作为,昏庸误国,弘光后投奔鲁王、唐王,也没得到重用,但他仍身体力行,亲自带兵上战场,多次参加攻打杭州的战役。即使被鲁、唐两王拒之门外,坐定奸臣的罪名,他依然始终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战斗到最后也拒绝投降,始终坚持抗清,直至被俘而死。从这一点来说,不失为一个悲壮慷慨之士。自当时人如复社人士沈士佳开始,后之人及有关书籍,就对马士英有了一些比较中肯的评价。沈士佳在《祭阮文》中认为,马士英是堕落于阮大铖,是“术中不党,愧悔为所用而事已去矣”,说马士英后来已后悔与阮大钺的交往,但为时已晚。《清实录》及清廷内部档案也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过钱塘江进攻余杭、富阳清军的战斗,他在太湖抗清的壮举,如前所述。数百年后的民国时期,贵州安顺姚大荣 才撰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专为马士英翻案,书中从多方面还原了马士英,可惜仍未消除学术界和历史人物研究领域对马士英的偏见。但有的研究者在马士英抗清问题上,还是作出正确的评价的。著名史学家陈垣说 “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钺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贵州先贤邢端也肯定马士英在抗清中是“百战不屈”而死的。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首先在贵州,然后至相关省份和学术领域,才开始对马士英的全面研究,以论文、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对其给予比较公 平、正确的评介,研究课题集中在马士英是否“阉党”“汉奸”,重用阮大钺及其身世、戚属等方面,也有涉及其诗文、绘画的,应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