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王士俊:进士出身任翰林官督抚 获孔雀花翎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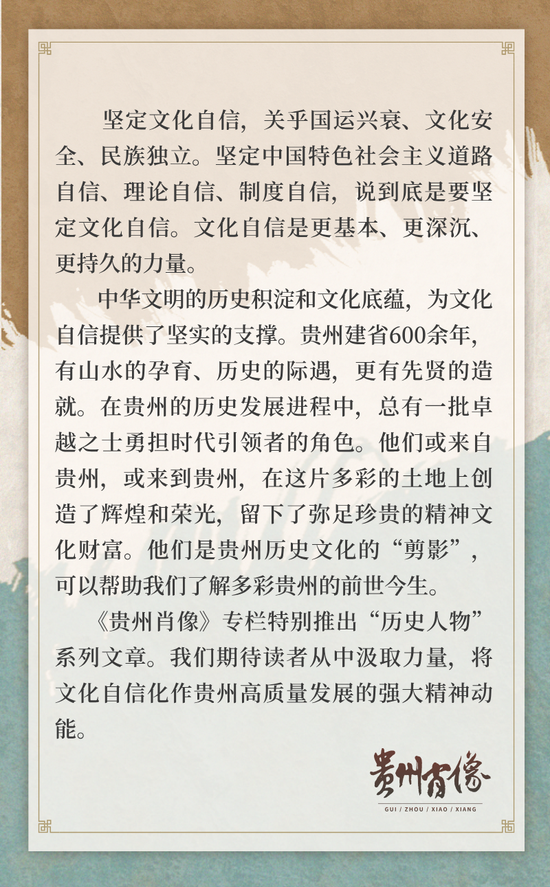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王士俊:进士出身任翰林官督抚 获孔雀花翎第一人
王士俊,清雍正朝名臣,政治家、学者,河东总督,终官四川巡抚。字灼三(一作野君),号犀川。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贵州平越府牛场里(原属瓮安,今属福泉县)渚浒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父王梦麟,举人,曾任丰润(今属河北唐山市)县令,“有政声”。
王士俊“10岁即能诗善文”,聪明好学,“见事不平,据理争辩”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23岁,因“乡试不售”,便到丰润县探望父亲,一面帮父亲做一些文书事项,一面也研习朝廷律令,熟识政务吏治。后返乡,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考中举人,六十年(1721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人翰林院(是年,其叔父王梦旭、王梦同时入翰林院,故称王门“一朝三翰林”)任检讨从事。雍正元年(1723年),特旨选送河南以知州用,不久任许州知州,自此开始其官宦生涯。后历任祁县、祥符县,“勤政爱民”。雍正三年(1725年),王士俊得广东巡抚杨文乾赏识,奏准朝廷后即随之广东,任琼州(今海南)知府、分巡岭西道。四年(1726年),任肇、高、廉道,旋署理广东按察使。五年(1727年),由于王士俊廉正不阿,得罪不少广东本地官员,这些人便以不能任事参劾他,但雍正皇帝“洞烛其私”,认为他“尚为有用之员”,下诏回京。未到京师,即命回广东署布政使。次年,升任布政使,钦赐貂皮绸缎,得“专折奏事”特权。八年(1730年),主修《广东通志》。次年擢升湖北巡抚,并得到雍正皇帝三次召见。十年(1732年),王士俊调任河东总督。十一年(1733年),王士俊受命兼任河南巡抚,主修《河南通志》。十二年(1734年),因政绩突出,皇帝特赐孔雀花翎。清制,凡进士出身而任过翰林院职务的官员,皇帝是不赏赐孔雀花翎的,故曰“本朝翰林官督抚,从无赐翎者,有之,从士俊始”。自从王士俊得此殊荣后,雍正以后历代皇帝才开始赏赐翰林出身的臣下孔雀花翎。
十三年(1735年),因河南开垦田土事,遭劾回京,任兵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以兵部侍郎衔署理四川巡抚。当时,成都多次火灾,500余灾民无处栖食,即捐银500两赈济。八月六日主考乡试,捐银150两为考生购肉米之费。是年,密疏四事,被以“越职言事”,撤职下狱。部议“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奉旨“改斩监候”。次年诏“削职为民,饬令回籍”。王士俊回到牛场后,出资修建文昌楼,将携带回来的万余册书收藏楼上:供学子阅读。自己则“遂日耽心学,从此亦渐忘情於仕,闭门复理旧业,贯穿经史百家,力求周陈张朱渊源,日增向所未至,心性之学,愈见真确,绝迹城市,环堵萧然,泊如也。”
王士俊官声卓著,博学多才,善诗文,亦有学术著述传世,计有《河南山东古吏治行》《河东从政录》《粤藩承宣录》《抚楚略》《吏治学古编》《年齿录》;编有《犀川诗文集》《读书半解》《读书小疑》《理性述》《闲家编》《困知录》等著述,其中《闲家编》一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主修《清流县志》《广东通志》《河南通志》等。王士俊工书法,开封试院内有其所题匾额“月华纪瑞”,贵州福泉有他题撰的《重修平越府学碑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王士俊病逝于家,享年65岁,归葬牛场祖茔。
王士俊一生从政,所至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兴利除弊,废除向新官送银陈规,禁止向他送礼,紧缩库银开支,人民为他书赠“清洗十万赃名”条幅。他体恤民情,关心人民疾苦,每到一地,都为民请命,减轻人民负扭,并亲督兵民护堤防汛,捐资银两,救济灾民。他公正无私,大胆办案,擒获真凶,沉冤得昭雪。每当他离开一地时,万民跪于路旁洒泪挽留。在许州时,因黄河经常决口,地方河防物资年年缺乏,灾荒时时发生,百姓困苦。王士俊“革除衙门买卖官价,国课重耗,派办物料等除规”,以市价买卖防河材料,并“严惩盗贼,平反冤狱错案”,“减免赋税,鼓励农耕”,百姓生活得以缓解。在调任河南第一县祥符离开许州时,百姓感恩,依依不舍,“拥留有脱轮断镫之风”。王士俊到祥符后经调查,与巡抚据理力争,并说“官可不做,民命不可不恤”。后经朝廷复查,最终免去祥符民工每年帮堤工银二万余两,百姓又得复苏生息。在湖北任上,王士俊经了解后立即禁止了原湖北官场上下属向上司送礼之歪风。当时,衙门内有公费外余款银二万余两,向来均被督抚等官员私分享用。王士俊则认为,官员“廉俸外皆非所应得”而坚决不接受这种额外银两,并奏请朝廷,将这一部分款项收为库存,作为防修长江大堤之用。在广东,王士俊不畏强势,弹劾署理巡抚阿克敦、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愿瑛等“结党朋谋,徇私灭法”,经朝廷派人复查,阿克敦等人“俱论罪如律”。王士俊任河东总督时,兼任河南巡抚,因“直声久著,山东、河南郡县畏之,甚于巡抚,贪污敛迹”。他又根据赋税钱粮、地方安全等,对当时山东、河南的行政区划,提出调整归并等建议。他在奏疏中说道:“东省旧设卫所,屯地分布各州县,相距甚远,崔征输纳俱有未便,请将莱州府属之骜山、灵山二卫守备,浮山、雄岩二所千总,俱行裁汰,改设巡检把总等官屯地钱粮归并附近平度、胶州、即墨、高密四州县征收,各屯户与民一体排甲编审,仍注明卫所字样,以免牵混。”“豫省陕汝二州,河南一府,距省甚远,为极西藩篱,请增设河南陕汝道,以资弹压”,均获得朝廷同意,这是山东、河南两省在雍正时期行政区划的一次较大变动,王士俊所奏《请总督住兖州疏》专论其事,故功不可没。另,山东荣山县的设立,也在王士俊河东总督任上。
王士俊在雍正后仕途不进而反遭挫折,始于乾隆初年重议河南开垦田土一事。先是,田文镜在河南督促州县开垦荒地,王士俊继任后继续行,且督促更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在豫三年,贻累民间”。故遭户部尚书史贻直等人的奏劾,上谕以王士俊“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虚名,成累民之实情”,“着解任来京候旨”罢官。当时河南开垦田土,究竟对否,至今学界仍有异议。对此,有人评论:认为“王士俊作为这一开垦案的主要责任人,在开垦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他担任河东总督这一段最辉煌的时期里,也是开垦弊端最多的时候。在河南期间,为了报答皇帝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是向皇帝表现他的才干,王士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坚决执行雍正帝的开垦政策上。由于雍正大力鼓励开垦,同时加上雍正用人政策对当时官场产生的强大刺激,以至于官场出现以苛为尚的风气,官员出现以苛为贤的标准。甚至,评价官员贤否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他在任上开垦了多少土地。在这两重因素的作用下,官员们纷纷效仿王士俊,用尽全力来督促开垦,结果许多省份纷纷出现了虚报捏报的情况,于是开垦案便发生了。而在开垦的过程中,以王士俊为代表的一批官僚们在皇权的作用下逐渐转变成‘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只知有君不知有人’。于是在开垦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累民的弊端,像王士俊那样的开垦案在新皇帝乾隆即位后被揭露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而新皇帝面临的将是对前朝弊端的革除和对前朝政策的调整,作为雍正朝开垦的典型也是被弹劾最多的王士俊,在河南的开垦便首当其冲成了新皇帝推行新政的靶子。新皇帝也以此为契机调整前朝的开垦政策,革除苛刻的官场习气,重塑官场规范。”故王士俊遭到解职,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后王士俊在四川巡抚任上,密呈四条对时政的建议,又使乾隆震怒,以致“解士俊职,建下刑部狱,王大臣等会鞫,请用大不敬罪拟斩立决,上命改监候”。于乾隆二年(1737年)削职为民,遣归原籍,结束他的政治生涯。
清代用人向重科第、资历,一个人中进士以后人翰林院,后再谋取外任地方官或到内阁六部任职。要做到督抚,至少得有二三十年时间。而王士俊十年之间就从州县升至封疆大吏,在清代200余年里是少有的,一方面是他本人彰显出其惊世才干,另一方面是雍正皇帝用人不重科第、重才能,故才有王士俊的担当大任。史称“(王士俊)不畏强御,世宗皇帝不次用人,士俊被特达之知,与李卫、田文镜并称”,同为雍正名臣,称誉于世。王士俊为官从政,却清廉一生。他自回到原籍至逝世,“数遭家难,囊中无资”,死后更无一点家产留给后人。后来,被他拔擢赏识的刘藻在云贵总督任上,曾派出使者,前来祭扫王士俊墓,并“赠金三百”才得以解决其子孙之贫困。王士俊从政仅仅16年,官至封疆大吏,但他从不畏惧强权,凡他所到地方,“必以兴利除弊,摧锄奸贪,忠精于济,百折不回。卓然为一代名臣所不愧焉!”这才是历史给他的公正评价。
王士俊所辑录的《闲家编》一书,杂引古书,参以已见,均为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经典语录,有较高的理学价值,是进行传统儒学教育的主要参考书籍。是书共八卷,王士俊自己说,这是他“编撷旧闻,旁参臆见,钩贯联缀,分部就班”而成,以为治家垂范。全编分家训、家礼、家政、家壶等共八卷。在《闲家编·家政》中,王士俊提出“饥寒小儿安乐法,饱暖小儿疾病根”的理论,对家庭和家长溺爱儿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其中一段:“抱儿者常令之采打人以为欢,甚至父母引手令击其面,或动出淫喋语以詈人。此乳婆、愚父母之通病。”这段话,可说是中国思想界较早提出育儿理论的。王士俊还搜集了不少前人语录,编入《闲家编》中,对人们提出一些做人的要求。如“林之木不足以胜双斧。万金之子不足以当坐费”(《闲家编·警言》引崔铣语);“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闲家编·箴言》引吕得胜语);“内要伶俐,外要痴。聪明逞尽,惹祸招灾”(《闲家编·箴言》引吕坤语);“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闲家编·正言》引范竹溪语)等。此类语录,言简易懂,受益匪浅。吕得胜,吕坤、崔铣、范竹溪等,均为明代思想界知名人士,所著《女小儿语》《小儿语》《呻吟语》《实政录》《招良心诗》等著作都通俗易懂,故王士俊在《闲家编》中普遍引用其中语录,以之作为人们治家育人的经典警句。(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