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护国战争将领戴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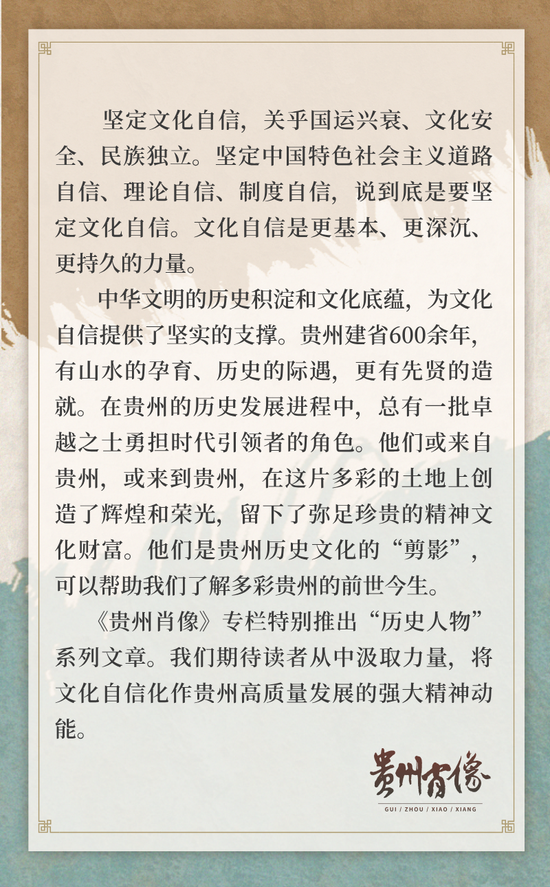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护国战争将领戴戡
戴戡,护国战争著名将领,民国时期贵州、四川省长,追赠陆军上将。初名桂龄,字循若,号锡九。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贵州省贵定县昌明区猴场堡人,为农民家庭,父戴连城,母钟氏。光绪十六年(1890年),戴戡12岁,母亲病逝。其父带着戴戡回到老家贵定旧治镇,戴戡拜镇上名师、当地宿儒郎云程为师。郎云程与戴戡一见如故,他见戴戡有表达语言能力极强的天赋,将之收为关门弟子,并与其儿子郎世香同吃、同住、同学习,“相互砥砺,经常切磋”。在郎云程的精心教导下,戴戡“苦读三年,如坐春风,进步极快,初次乡试便锋芒展露,一举考中秀才”。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郎云程送儿子世香到贵阳,投晚清西南学派大师徐天序门下学习。郎云程因不忍戴戡被世俗生活所埋没,便借口让戴戡陪伴儿子世香读书而一同“负笈进省”。巧的是徐天序对戴戡也是一见如故。不到一月,戴戡就一鸣惊人地考得了贵州赴日留学生名额,时人有“贵定县旧治镇出神童了”之誉。戴戡得到郎云程及贵定乡绅的经济资助,赴日留学。最初就读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专科,一年后毕业,又考入高等理化科。在日本期间结识了梁启超、蔡锷等人,并加人梁启超在日本组织的“政闻社”,为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戴戡在日本宏文学院高等理化科毕业。此时,其恩师徐天序病危,戴戡便决定回国探望。之后在同乡陈国祥任堂长、熊范舆任教务长的河南政法学堂执教,分管庶务。宣统元年(1909年)回贵州襄理矿务。宣统二年(1910年),受熊范舆的举荐,并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到云南省经办锡业矿务,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宣统三年(1911年),戴戡为料理父亲丧事回乡,时值辛亥革命,戴戡因与云南省蔡锷等关系密切,又是贵州宪政预备会的骨干成员,被聘为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员兼军政股副主任。此时,宪政预备会为了进一步独揽黔省大权,派戴戡亲赴云南向蔡锷“乞师援黔”。民国元年(1912年),任唐继尧时贵州军政府左参赞、黔中观察使。次年,任贵州民政长,旋改巡按使。民国4年(1915年),为云南、贵州间反袁联络人,云南独立,任护中国军队右翼军司令。次年,率护中国军队进人贵阳,鼓励黔中父老参加护国战争。率军进人四川,予北洋军重创,任中华民中国军队务院抚军。同年,任川东巡阅使,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省长。
民国6年(1917年),在四川与张勋特任“四川巡抚”的四川军阀刘存厚交战,史称“刘戴之战”。戴戡所率黔军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兵困无援,其部将黄大暹、张承礼当场被乱枪打死;熊其勋化装成民夫逃至简阳被川军俘虏,押回成都后被刘存厚斩首;雷飙躺在死人堆中装死,侥幸活命。戴戡战败,于7月21日,逃至仁寿县小陶家湾秦皇寺,又被川军四面包围,眼看已无生还希望,便于绝望中拔枪自杀(一说为川军吴庆熙部击毙),死前戴戡留言:“我与共和同生死,今不幸遭逆贼叛国,为贼所算,我不可受贼辱。我死后,为我语同志,恢复共和,即为我复仇也。”时年仅39岁。8月17日,北洋政府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表彰他自辛亥革命以来“联滇定黔”“拥护共和”的功勋,以及入川后“见危受命”的业绩,同时令国史馆为立传,并由财政部拨付白银1万两治丧,灵柩运回原籍,葬于贵定县旧治镇大学坡。梁启超题写挽联:“智不感、仁不忧、勇不惧,推翻帝制,计出万全;捍大患、定大策、决大疑,有数人才,又弱一个。”
民国元年(1912年)“二·二事变”后的1月27日,蔡锷命唐继尧带兵,挥师直指贵阳,于3月2日攻古贵阳,推翻大汉贵州军政府,唐继尧为贵州部督,戴械为左参费、黔中观察使等。民国2年(1913年)11月1日,北洋政府任命戴戡为贵州民政长,后政为巡按使。由于戴戡与云贵上层关系密切,被立宪派称为“奇士”,护国战争爆发前,是梁启超、蔡锷在云、贵方面的重要联络人。民国4年(1915年),戴戡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密谋倒袁护国,参与谋划云贵起义、戴戡自此成为梁启超、蔡锷在云、贵方面的“首要联络人”,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更加亲密,成为进步党的活跃分子。他经常与蔡锷的电联系,蔡得也向戴戡通报京中情况。9月3日,戴戡接到蔡锷“以势测之,为期不远,望早进京,共商大义”的密电,即与挚友王文华等人商议大事,并亲自“编制专用密电码”,以便“一旦发生变化”时,确保北京与贵州之间的联络畅通。之后,戴戡借与刘显世难以相处之由提出辞职,在得到袁世凯准辞后,便按照与蔡锷商量好的计划离开贵州,赴北京任参政院参政。同年,梁启超、蔡锷、戴戡等人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蔡锷、戴戡摆脱袁世凯监视尽快回到昆明,起兵讨袁。戴戡由天津到香港、蔡锷绕道日本在香港与戴戡汇合。12月18日,袁世凯电唐继尧:“蔡、戴来滇可便行事,就地正法。”唐继尧未听,反而于12月19日,迎接蔡锷、戴戡等人进人昆明。随即在都督府召开讨袁会,决定组织护中国军队出师讨袁。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中国军队总司令部,戴戡任护中国军队右翼军司令。期间,先后发出《通告全国共同劝告之漾电》《为声讨袁世凯宣布独立致电各省通电》《哲告全国声明护国宗旨书》等电文,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讨袁。民国5年(1916年)1月3日,戴戡与徐进率护中国军队先遣纵队由昆明出发,当纵队进抵黔边时,遭到黔军阻挡。1月12日,纵队进通盘县县城,戴劝说驻守盘县的黔军团长易荣黔起义,参加护中国军队。易荣黔在戴戡、张彭年等人劝说下、同意起义。与此同时,云南方面恐贵州反对滇军入黔,亦增派力量声援戴戡。1月24日,戴城率纵队抵达贵阳,对贵州决策者刘显世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戴戡一方面向刘显世等介绍反袁斗争的形势,促使内部分化,另方面又积极向各界群众宣传,争取群众的支持。1月26日,戴戡在贵阳各界数千人的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鼓励黔中父老当机立断。他慷慨陈词:“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后已,岂有他哉!再论到成败一层,袁世凯既已众叛亲离,不亡何待!”戴戡的演说,道出了贵州人民的心声,得到热烈拥护。黔中人民称他是“不为爵禄所诱,除阻所难,薄富贵尊荣之参政不为”的反袁义士。他的演说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贵州反袁运动的发展。
民国5年(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独立,并参加武装讨袁。次日,蔡锷、唐继尧、刘显世联合任命戴戡为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将贵州出征黔军一律改编为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下辖东路、北路黔军。几天后的2月3日,戴戡率领刚刚组建的滇黔联军北路军梯团4000多人,在贵阳各界人士敲锣打鼓的热烈欢送下,全军在“铲除帝制,还我共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雄壮誓师声中开拔遵义,奔赴黔北门户松坎镇,投入到护国战争中的川南战场,以进攻綦江、扼守綦江,从侧翼威逼重庆,配合护中国军队川南战场整体行动为作战目标。2月8日(说13日),戴戡一行抵达黔北桐仁松坎镇,立即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并在松坎设司令部坐镇指挥。指挥护中国军队右翼北路军与北洋军曹锟部的吴佩乎旅作战。此时,袁世凯在綦江布下了重兵,在川黔交界处的兵力达五六个团,而戴戡率领的滇黔护国联军仅有两个团4000多人的兵力。2月14日深夜战斗打响,护中国军队向綦江前沿阵地吴佩乎部发动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重创北洋军。期间,为了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戴戡于3月15日发表了《劝告北军将士书》,用政治宣传来瓦解敌军。为此蔡锷曾赞叹曰:“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这时广西、广东、浙江也先后宣布独立。5月,孙中山率国民党在上海发出第二次讨袁宣言,在肇庆成立中华民国军队务院,推黎元洪为大总统,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锣、戴等人为抚军。加之,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等人也倒戈一击,四川、陕西、湖南纷纷宣布反袁独立。袁世凯在惊恐之中,于6月6日忧惧而死。之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6月29日颁布《临时约法》,恢复了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并宣布历时两年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委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7月7日,北洋政府也任戴戡为贵州省省长。鉴于护国运动前在贵州巡按使任上曾遭刘显世排挤,此时此刻刘显世的势力仍然很大,戴戡不愿意任贵州省长,通过梁启超的疏通,加之护国有功,改任川东巡阅使。后蔡锷以病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北洋政府于9月13日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10月7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戴戡为四川省长,戴戡遂在重庆、綦江一带扩充黔军实力。民国6年(1917年)5月,北洋政府发生了“府院之争”。6月8日,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逼大总统黎元洪下台后。7月1日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旧制。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出兵讨逆。戴戡及时得到梁启超电示,当即通电反对复辟,拥戴共和。7月3日,张勋以议政大臣名义特任四川军阀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授三等男爵。但刘存厚因反对复辟之声猛烈,不敢轻易就任,暂存观望之态。这就给戴戡进攻刘存厚提供了口实。此前,戴戡以邮电检查为名,控制了刘存厚与外间的通讯联系。同日,戴戡率黔军熊其勋部进驻成都皇城,并立即督军署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知刘存厚到皇城以应对张勋复辟而共商国是。但是刘存借口他由派代表吴绍良参加会议。戴戡要刘存厚的代表吴绍良明确表示对张勋复辟的态度。吴因未得到刘存厚的指示,不置可否,却王顾左右而自他,请求撒销邮电检查。戴戡不允,坚持要刘存厚的军队立即移驻川北,双方因此剑拔弩张。戴发急电唐继尧、刘显世,主张“合滇军力”,对刘存厚“先予痛剿,免碍进行”。7月4日,唐继尧、刘显世、周道刚、熊克武联名通电声讨张勋。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也虚张声势发出讨逆。刘存厚得知这一消息,慌忙发出反对复辟通电,在舆论上争取主动,使戴戡失去讨伐口实。但此时戴戡进攻川军的准备已经充分。7月5日,川、两军在成都发生战斗,酝酿多时的“刘戴之战”终于爆发。以戴戡为首的黔军先发制人向市内川军发起进攻,以7个营的兵力扑向川军。而此刻滇军却按兵不动,一心想待川、黔两军精疲力竭时,再卷土重来。黔军得不到声援,而川军却在源源不断地由2个营猛增至5个团,向黔军反攻,黔军很快陷于被动局面而被打败。7月15日,戴戡见滇军未到,走投无路,同意由四川省议会调停,自愿交出省长、督军、会办三颗印,请求允许败军退出成都。7月20日,戴戡“苦守十三日,终致不支,乃挂印于省议会,乔装突围,出南门”,退出成都,沿途遭遇川军伏击。7月21日,行至仁寿县附近的秦皇寺,兵败自杀。此次“刘戴之战”,戴戡部“熊其勋、张承礼、黄大暹与俱死,黔军五千人覆没。是役,毁民宅三千余,百姓死伤六千余”。(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